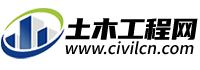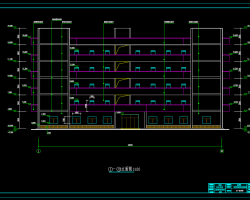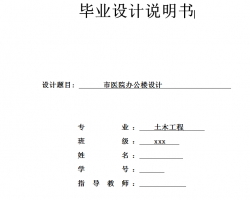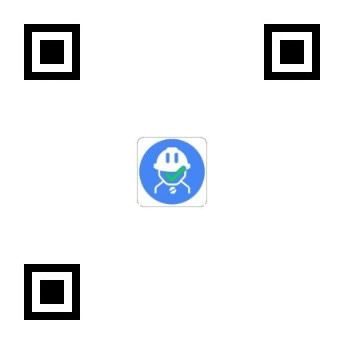一、建筑及城市规划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
我国的大学校园建设开始是以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校园规划理论为指导原则的。建国以后,根据经验,结合国情,确立了以功能分区为核心准则的校园规划理论和规划指标体系,指导了我国现有的绝大多数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然而,那些曾被奉为经典的校园规划理论和规划指标体系都是建筑、规划界的学者站在自己学科视野中的阶段性经验总结,是相当不成熟的,至今,这些欠成熟的校园规划理论仍是我国大学校园规划建设的根本依据。在理论欠缺的情况下,建筑、城市规划领域对大学校园的研究只能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
随着近几年高教改革的深入,校园建设188金宝博平台量比过去翻了几翻,建筑和城市规划界开始频繁关注大学校园建设的理论建构。2001和2002年在北京和台北分别举办了“海峡两岸‘大学的校园’研讨会”,在大陆和台湾的建筑规划界掀起了大学校园的学术热。与以往相比,两次会议的论文开始重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大学校园建设的历程,不再局限于校园188金宝博平台的阶段性总结。
一些建筑学者开始关注高等教育思想对校园建设的影响,只是他们的观点阐述不太系统,只能说是一种“散见”。如:《大学校园规划结构的研究》一文认为“大学校园形态与大学当时的办学理念、教学制度和内容是一致的”。如中世纪的大学主要职责是培养神职人员和为王室服务的人才,大学校园必须是封闭的,能够使学院排除外界各种影响,完全服从教会,校园生活充满清规戒律。因此,校园多附属于教堂或修道院,或者以宗教建筑为样本进行设计建设。19世纪工业革命后,美国高校将学术自由理想和为社会服务的办学宗旨相结合,创立了独特的高等教育模式,也创立了影响全世界的开放式校园形态。20世纪后期,教育体制走向多元化,校园形态也越来越多元。这种对教育思想和校园建设关系的描述,虽然稍稍打破了一点建筑界习惯性思维的限制,但依然停留在对高等教育理论浅层次的理解上,并没有阐明在大学校园形态演变中表现出的教育与建筑之间的互动关系。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些建筑学者除了对校园形态的“过去时”进行归纳总结外,对于校园的当下形态和未来趋势也作了一定分析探讨。一部分人认为,大学城将是我国大学校园在新时期的某种发展趋势。“大学城”是国内近年来新兴的概念之一,至今并无确切定义。一些文献资料认为,“大学城”是一种特殊的城市化方式,其发展模式大致分为“传统学术型”、“商业创新型”,或介于两者之间。前者多起源于历史悠久、具有强大学术号召力的一所或多所大学,经过漫长历史时期,逐步形成了校城交融的自然环境,如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城,德国的洪堡大学等。“商业创新型”大学城起源于新兴的理工科院校,以科技创新与市场紧密结合,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如美国“硅谷”和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关村则兼有二者的特征。
虽然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对大学校园建设起重要作用,教育界每一次大的运动都在校园形态上留有痕迹。但是多数情况下,建筑界与高教界的对话局限在建筑工作者面对高教体制改革所作出的单方面呼应。在现代教育哲学的指导下,现代大学不断构建着新的教育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对校园建设有一定影响;可这种影响对建筑界来说是被动的,因为建筑界还没有系统地探讨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与大学校园建设的关系。凭着对教育思想一知半解的领悟,喊几句时髦的教育口号,校园建设只能停留在肤浅的、“闻风而动”的层次,不可能有深度。
总之,当前建筑和城市规划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大部分是针对我国大学校园建设的实际问题提出的,研究思路也是围绕这些实际问题展开的。他们本着务实精神对教育界的热点理论进行可行性探讨,从建筑和规划的视角提出方案、进行实践,为新时期大学校园形态的发展作出有益的探索,也为下一步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氛围。
二、高等教育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
大学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一直是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学科领域对大学的研究多集中在理念、制度、机构等非物质层面,很少关注大学的物质实体——校园,即使有所触及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同大学校园形态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校园文化”的研究领域。
校园文化是置身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中的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亚文化形态,它渗透到学校的各个方面,涉及到全体师生员工的观念和行为。高校校园文化是在“大学这一特定的环境氛围内生活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校园价值观和这些价值观在物质与意识形态上的具体化。它的主体是包括学生以及教师、行政人员在内的大学校园文化群体;它的内容分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大层面: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深层文化,包括师生员工的价值观念、文化素养、心理素质及校风和校训、学风和教风、学校的传统习惯、校内文体活动等,物质文化包括校园建筑特色、文化活动场所和设施、校园绿化美化、学校的信息传媒等。校园文化的核心是校园价值观”。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到教育学者们倾向于把校园形态划分到校园物质文化领域。
过去,大学校园形态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一直被忽略着,被忽略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大多数人认为:建筑与教育没有多大关系。是的,建筑没有以“知识”的身份、“课程(狭义)”的姿态进入人们的“学习”视野,但它对人的教化作用是“知识”和“课程”所不能给予的。这一点,中国古人深有体会:《三字经》的头几句,“昔盂母,择邻处”可谓家喻户晓。正是孟夫子本人,亲身体验到环境对人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作出了“居移气,养移体”(《孟子•尽心》)的总结。中国古人早就懂得环境对人的“模范”作用,环境就是“模”,就是“范”;使用什么样的模范,就可能塑造出什么样的人物。英国首相邱吉尔也讲过“先是人创造了建筑,建筑反过来创造人”,非常准确地表述了建筑与人的关系,暗示了建筑的“育人性”。
当前,教育界在反思现代教育中的弊病时,把环境的教化作用提到了哲学的高度。金生在《理解与教育》一书中谈到“在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的冲击下,现代教育本身也被工业化和技术化,学生被纳入教育生产的流水线,与日常的生活世界相隔绝”。面对这个现实问题,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呼吁到:“人类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教育的研究都来源于并且归根于实践生活世界的需要”,“对教育的认识并不是一种事实的因果关系分析,也不是把人和教育作为孤立的客观对象去解剖,而是在现实的‘生活世界’
中理解和解释,也是‘同情’与‘参与’”。狄尔泰指出“理解和解释是贯穿人文科学的方法”。人文学的对象是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而生命总是具有意义并且要不断需求意义的,所以它就需要不断地理解和解释。这种方法把研究活动、研究过程看作是解释者和被解释者之间不断进行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使研究者直观地体验和把握对象的内在精神。学生在校园中生活、学习的过程就是与周围环境不断对话的过程。大学校园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充满意义的“生活世界”,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意义形式”,学生生活在其中,通过理解和解释与之“对话”、“交往”,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教育不知不觉进入学生的精神整体。大学校园形态就是一种教育表达式。
对于大学校园具有的“教化”作用,教育课程理论也有所触及。在课程理论中,校园建筑、文化设施、绿化设施、文化生活、校风、学风、人际关系、环境氛围等都属于“隐性课程”,与其对应的“显性课程”是指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技能、思想观点、行为规范等。同显性课程的明确性、强制性相对照,隐性课程的特点是:(1)潜在的规范性。无论是校园建筑、文化设施或校风、学风都潜在地蕴涵着一定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精神境界,使生活于其中的受教育者感受到应如何调节自己的心理和行为。(2)非强制性。不通过强行灌输、纪律约束,而是通过陶冶和感染,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净化人的心灵。(3)作用的持久性。即使生活环境变化或迁移,已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仍能长期保持。我认为“隐性课程”也包括“隐性”和“显性”两个状态。校园形态属于“隐性课程”的物质方面即显性形态,而校园形态所构成的文化氛围,所凝聚的价值观念,所包容的文化生活则属于“隐性课程”的精神方面即隐性形态。对于隐性课程的规范系统的描述和研究以前在我国教育领域不多见。
最近几年,教育界的学者开始用跨学科的方法和视角研究“隐性课程”中的“隐性形态”,如南京师范大学的刘云彬博士进行的学校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等。但是对“显性形态”——大学校园的系统研究一直被忽略着。
三、大学校园研究的紧迫性
就全球普遍的时代背景而言,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学改变了以往作为社会产品和最终用户之间的中介身份,不仅承担着教学科研的基本任务,更成为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主要环节。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强,功能也越来越复杂,大学校园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我国大学校园的现状在数量、质量、规模上都相对滞后,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培养高等人才的能力,大学校园建设(改建、扩建、新建)工作迫在眉睫。
时代在变,大学的功能、职责、理念在变,校园建设的理论指导当然也要“与时俱进”。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高等教育界、建筑和城市规划界的专家学者打破学科壁垒,站在跨学科的视角对大学校园进行系统研究。因为理论的苍白将导致实践的浮躁,校园建设的失败必然会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希望高教界对大学校园的理论探索中多一点对物质形态的关注,改变一下教育研究者在校园建设中的“失语”状态;希望建筑界对大学校园的理论研究多几个视角,改变一下建筑人在校园建设中的“自语”状态。
参考文献
[1]姜耀明,王晓丹.大学校园规划结构的研究[J],新建筑,2002,(4).
[2]王吴.弹性与共享:大学城规划[J].规划师,2002,(5).
[3]胡智丹.关于有效控制校园文化整合方向的几点思考[J].江南学院学报,2001,(9).
[4]张良帛.匠学七说[N].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5][6]金生钹.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